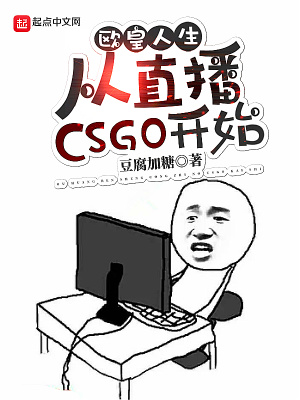无量阁>小炮灰蠢笨却实在漂亮[快穿] > 4050(第30页)
4050(第30页)
而稳当安静的车厢内,桌案上摆着精致的錾花暖炉。
大病初愈的温予白身着素色狐裘,清俊脸庞略显苍白,他眉眼低垂,视线落在玉质棋局之上。
纤长的眼睫遮挡些许光亮,看不太真切眸底的浅淡情绪。
无形中透着一股拒人以千里之外的冷然疏离感。
清瘦而骨节分明的手指执起一枚黑子,忽而停顿至半空中,迟迟未在棋盘落定。
温予白记起上一世曾听父亲说过,废黜储君的圣旨是在镇南王的接风宴上毫无征兆宣读的。
似乎宴会后,太子殿下的瘾症还犯了。
不过,前世温予白错过了这场宫宴,并不知晓具体发生了什么,且当时太子被废,局势徒然转变,丞相府也跟着被有心人发难,他无瑕顾及其他。
而今细想来,圣上明明向来好面子,却选在手握重兵的异姓王觐见时,以私德有伤为由,大张旗鼓地废黜太子。
——这有些说不通。
温予白眉心微拧,适时一旁没关严实的车窗帘布猝不及防透进一道凌冽寒风。
他绸帕掩唇轻咳了几下,领口狐裘绒毛也跟着颤动。
边上候着的丫鬟慌忙去压合上帘布,没忍住嘀咕道:“别怪奴婢多嘴,可公子您就该和老爷乘一架马车入宫,干嘛委屈自己坐这寒酸的……”
温予白未接话,他有自己的考量。
父亲丞相的官衔摆在那儿,不可避免被各方势力盯着,若与之同行,此番入宫行事只怕多有不便。
更别提,除了观察镇南王是否和那个叫安然的小太监有交集外,温予白还打算宴后去寻太子殿下商讨一些事宜。
故而,越是不惹眼越好。
丫鬟还未絮叨完,伴随着铿锵有力的密集马蹄声,好似听见有人谄媚地叫了一声‘镇南王’。
温予白若有所感地抬眸,指尖拢了拢厚实的狐裘,道:“把帘布掀开。”-
风雪稍霁。
宫门前查验腰牌的侍卫们动作仍然迟缓,不少官员权贵的马车拥塞得不能动弹。
不远处,一队人马疾驰而来。
彪壮黝黑的马匹在京都较为少见,粗犷坚韧的鬃毛被大风刮乱,罕见披着泛着寒光的马铠,隐隐带着摄人的压迫感。
从温予白的视角看去,为首的镇南王霍越眉眼凌厉危险,薄唇紧抿成一条直线,在狂躁的马蹄即将踹翻临近的车厢前,大手猛然狠拽,勒紧了缰绳。
烈马嘶鸣刺耳,前蹄高悬,马身倾斜,高大俊美的男人仍稳坐马鞍之上。
一些被吓坏的官宦女眷们还没反应过来。
而眼尖的人瞟见对方的腰牌,早就满脸堆笑着上前搭话了,却被直截了当地无视。
镇南王眉宇间裹挟肃杀之气,不怒自威,他扫视一周。
身下的烈马不耐地喷着鼻息,蹄铁暴躁地踩弄积雪。
急忙跑过来的宫门的侍卫领头冷汗直冒,讨好地指着特意预留的宫道。
“王……王爷,您这边请,走另一侧的宫门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