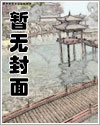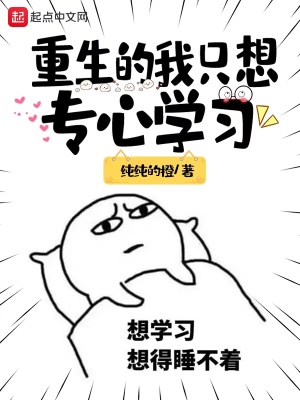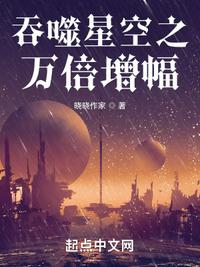无量阁>【完结】呼雪为君(校园1V1低H) > 老药厂(第2页)
老药厂(第2页)
“没错,而且我妈把时间也记错了!根本不是附中动土前做的法事,那得多早了啊!我跟教堂的老人聊天,其中有两个老人说,附中那群人是年做的法事。”
“他们又怎么知道的?附中在x安区,跟你们街道还隔着江呢。”
“我听说药厂是年年底搬走的,迁址的时候人员也改组了,有不少流向了江对岸。”
“也对,x昌区的医药研究所就在你们街道。年代初的就业环境一定比现在好不少吧。”
“也不一定,得看什么行业……哦还有,老药厂那边也有个教堂,他们还挺厉害的,有自己的唱诗班,自主创作的合唱曲目拿过几次国家奖项——扯远了,我的意思是江对岸的宗教活动比这边发展得好,教堂里的老人提起那边的事,可信度还算高。”
“明白了,谢谢你。”
银霁可以理解小田的妈妈为什么会有记忆错乱:“附中有人在周边的药厂做法事”实在太不常见了,结合流传于全国各地的“学校建立在乱坟岗上”这类传闻,很容易想岔成“有人在附中动土前做法事”。遇到难以理解、乃至反直觉的事件,人脑总会自动进行一些合乎日常逻辑的补完,这就是自发性记忆错误现象。上世纪三十年代,英国的一名心理学家做过一个“幽灵战争”实验,说的是……
“等等,我还没讲完。知道你会好奇,我就帮你多问了一句——既然是在老药厂做的法事,围观群众又怎么知道那群人跟附中有关系?然后,我就得知了一个吓人的真相,猜猜是什么?”
想象到屏幕那头小田期待的表情,银霁无奈道:“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个比较有名的附中高层。”
说完就有点后悔了——是不是应该配合他假装猜一下?最好是第一遍没猜对,等着他来公布正确答案,然后狠狠拍个马屁,让忙前忙后的人得到奖赏,达成一种心照不宣的和谐,掩盖关系上的不对等……罢了,银霁的目的单纯只是打探消息,才没那个闲工夫。
“还真是。”小田不会直说“没意思”,只把失望体现在打字速度变慢上,“我市第一辆捷豹就停在那附近,想也知道是哪位万元户。”
“年啊……郑校长还在任。”
“不是郑校长,郑校长多艰苦朴素的一个人啊,不可能像这样招摇过市的。那个时候药厂改组了,附中也想着扩建,不过到最后也没扩建得了,地也没盘下来,一直把废弃工厂留在那边,到现在都没拆,简直搞不明白这些城市规划者在想什么。”
这么说来,a市留着不拆的废弃工厂还真不少,银霁家附近就有一个。可能是沿袭了节俭的老习惯,希望这些稳固的建筑哪天再派上用场吧。
“虽然没能扩建,”小田接着说,“但不妨碍一些海归精英给母校捐楼啊!你要是认识附中的人,可以问问他们‘春蚕楼’的事。”
“‘春蚕楼’吗……好的。”银霁把目光投向书桌,那里放着雷成凤送给她的陨石。
至此,全部问题都得到了妥善解答。灭绝师太没能给到期望中的奖赏,小田也不想遗憾离场,因为他还能掏出一个共同话题:“对了,绿茶男的事你打算怎么办?”
“不怎么办啊,都按原计划进行。”
“还不放弃啊……啧,算我求你,就是真的要干,你最好准备两套方案。”
“不用,我心里有数的。”
“几个数啊你就……是梁静茹给你的勇气吗?”这句话跟着一个摊手摇头的表情包,是他昨天才从银霁用过的套组里偷走的,“没关系,你学习成绩好,怎么着学校都不会开除你。”
小田从一开始就不看好她的打狗计划,一有机会就唱衰,不过这回,他倒误打误撞说对了一件事,只是细节上存在一些误差—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