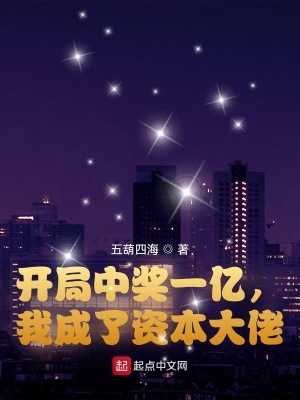无量阁>【农家厨女】带着空间逃荒发家 > 第220章 队伍崩塌(第2页)
第220章 队伍崩塌(第2页)
篝火越烧越旺,火光映红了小院,汪夫人借着火光,坐在小板凳上,手里拿着针线,仔细地缝补着布鞋,动作虽然缓慢,但每一针都缝得扎实。
“想不到这些时日奔波逃荒,我也有力气,能纳得动鞋板了。”
老汉们围坐在火堆旁,他们的脸上刻满了岁月的痕迹,手里拿着旱烟袋,一边抽着旱烟,一边聊着以前:“往年这会儿,都在准备窝冬了。”
“也不知道村子怎么样了,都怪那该死的县令!”
“这贡山县也挺好的,粮也不贵,天也冷了,瞧着这边没遭灾,俺都不想走了……”
也不知谁起的头,发起了牢骚。
“是啊!瞧我家那口子,可不像村长家,也不像汪大夫家有牲畜帮拉,全家的家当都在肩上。”
赵家娘子有些哽咽,“那手跟脚掌起泡,挑破了也继续走,走得那血糊一片,跟鞋袜都分不开了。”
“可不是,眼瞅着我家姐儿也要嫁人了,这么走怎么是个头啊。”
“就是啊,这里粮食便宜,租金也还行,要不干脆就定居在这里,以后等时局平稳了,再回村子里去。”
张家老族长本就不想背井离乡,还是惦记着早些回去。
一个人动了心思,想干脆留在这块,就有无数人附和。
“不成,这鞑靼还会再来的,这贡山县也不安宁啊!”
崔村长没想到大伙儿起了心思,听语气,话里话外还带着酸。
“什么叫有畜生帮拉!我们车上有大半,哪里不是放着村子里的物什?!”
崔大奶奶直心疼,这群狼心狗肺的东西,
“赵娘子,讲讲良心,你家娃腿疼了,也是我们把棉被腾出来,让他坐了好一路,你趁机把锅碗瓢盆什么重的也都放过去,那棉被可是我们老头子背了一路啊!”
赵娘子被这么掀了老底,觉着臊面子,她拉崔大婶子说:“你儿媳妇可是泉山村人,离贡山县也不算太远,干脆留下来,她也好见见亲家,你们也没多少牛车,总比一大家子苦兮兮去投奔外嫁女强些。”
“不成,我一定要去找温姐儿,起码看着她平安我才安心。”
崔大婶挥开赵娘子,她当初也是看着老村长一声不吭地还帮忙搬了一路棉被,最后去找汪大夫要了膏药贴膝盖。
没落到一声好也就算了,怎么还能把他们一起酸进来?
真是丧良心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