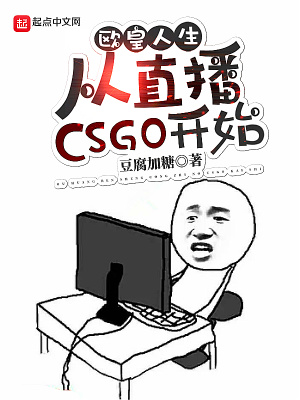无量阁>黑月光,但万人迷[快穿] > 第7章(第4页)
第7章(第4页)
祝砚疏上了车,才蓦然一怔。
他像是听到什么绝不可能从青年口中说出的话似的,陡然转头去看他。
两人其实是一个年纪。
同年同月同日生,又是被抱错的,更分不出谁先出生一秒。
所以本来不该区分哥哥弟弟。
但被认回祝家后,父母为了口头好区分,就让祝砚疏当了哥哥,玉流光当弟弟。
玉流光没开口叫过他哥。
祝砚疏也不在意,口头的称呼,没有一点实质性意义。
更何况被认回祝家后,玉流光一直没有答应上户口。
他现在的户口本依然只有一页。
突然叫哥。
车窗闭上,车内渐渐被暖气氤氲。
玉流光体质孱弱,畏寒,在暖的环境里脸色会薄红一些。
偏偏他又晕车。
关车窗时,吹不到清冷的空气,更容易晕。
玉流光偏头咳嗽,热气忽然覆上来,他垂着薄薄的眼皮,看见祝砚疏伸手拽过自己跟前的安全带,“咔哒”一声,插进凹槽里。
安全带系好了,贴在他手臂上的黑色外套却没有离去。
他闻到了祝砚疏身上清淡的药味。
生病了?
抬了下狐狸眼,视线里几乎被祝砚疏清俊的脸占据,对方面上依然不带表情,呼吸似是掠过他的颈侧,下一瞬,对方平声开口了,“荣宣对你做了什么?”
玉流光伸手按在祝砚疏黑色外套上。
他道:“好好说话,不要靠那么近。”
祝砚疏一顿,垂眼退回自己的位置。
他看向前路,手按在方向盘上,无知无觉下力道加重,手背青筋明显。
……变了。
如果是以前,他会拽着他的头发,冷眼问他凑那么近做什么?
荣宣做了什么?
才一个月,把人变成了这样。
车内沉寂几息,玉流光反手扎起了自己后颈上的黑发,“荣宣能对我做什么?就那样,你以为呢?”
祝砚疏将车开进市中心。
他平静问:“你们做了几次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