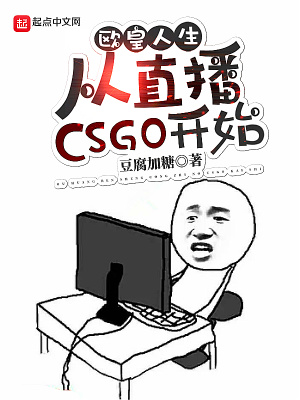无量阁>奈何他手段了得 > 4050(第10页)
4050(第10页)
视线错开。
谢恒逸心不在焉地点了支烟。
翅膀好了,鸟就该飞了。腿好了,人就该走了。这值得高兴吗?好像并不。
就这样放齐延曲走?好像不太甘心,他的报复还没报复到位,想做的事也没做到位。他用什么理由、什么手段能把人留下?
留下了就能甘心么?他甚至不清楚自己具体想对齐延曲做些什么。
烟雾在客厅散开。
他后知后觉想起了什么,随即将烟碾灭,掷进烟灰缸,然后从沙发上站起。
走了几步,僵硬的身体开始回血。他终于感知到落寞的情绪。
谢恒逸开了瓶酒,试图压下这些或低迷或高昂的情绪。他兴致缺缺地喝了一口,发觉枯燥无味,也放下了。
他干脆堵住还停留在楼梯口的齐延曲。对方问他要做什么,他僵持着不回话。
这个人,一点也不负责。他想。
明明是对方亲手酿造的这一切。如果不是齐延曲总这样那样,他怎么变成这样那样?
结果到头来只有他纠结执迷。
他早该想到的。这个人根本就是故意的,故意用这种手段报复他,想害他这几天都心神难安。
既然害得他睡不好觉,于情于理都该给他补偿。
过了良久,谢恒逸忽然问:“会用琴吗?”
“……不会。”
谢恒逸全然不管齐延曲回答了什么:“给我弹首安眠曲吧。”
他用的是打商量的语气:“行不行?”
齐延曲不再回答。答案很显然。
但很显然谢恒逸不在意答案。说话打商量不代表做事打商量。
他径直将人腾空捞起,箍紧那截腰身,简直蛮横,剧烈动作间齐延曲的手肘磕到他的下巴,他没反应,对方倒是吃痛地抽了一小口气。
他忍不住气笑了。短促炙热的吐息洒在对方耳畔,他察觉到对方在他怀中一缩,似乎失了挣扎的力气。
不过挣不挣扎的,影响都不大。他无视齐延曲断断续续的阻挠声,快步跨上楼梯。
为了保证稳,谢恒逸每一步都踏得很重。途经二楼时,他注意到走廊边上靠着轮椅,被折叠好的,单手就能提起。
他想了想,拍了下齐延曲的后背:“手上有劲没?”
齐延曲看了一眼轮椅,没明白他的意思。
谢恒逸今晚有种不知是人是鬼的诡异感,似乎很想捉弄他。就因为被他撞见在做那档子事?脸皮这么薄?
二十岁正是男性生理欲望最强烈的年纪,有这种行为再正常不过,有什么好恼的。
“不想摔就勾住我。”谢恒逸迟迟没等来回复,索性不等了,松开了左手。
齐延曲眼皮一跳,在上半身坠空前,他完全是凭借本能地环住男生绷紧的脖颈,指尖没入其后颈的发茬中。